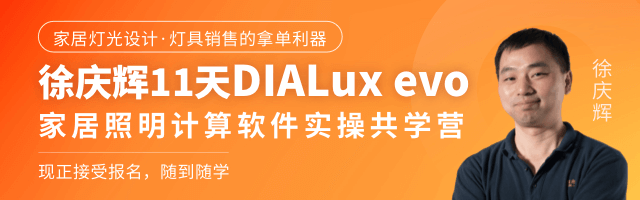编辑手记:
4月24日的时候,微课堂推送了一篇以《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城市地标 :哈尔滨大剧院照明如何设计?》的文章,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江海阳老师看到之后,颇有感触,于是投稿给微课堂,与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想法。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每一个有良知的建筑设计师都有两个情结,其一是自然主义,这表现在有机建筑,仿生建筑以及覆土建筑和节能建筑上;另一个就是设计的乌托邦倾向,设计师幻想人在建筑面前不被矮化,有足够的人性张扬和尊严。建筑与人的无限亲近,所以我们听到建筑师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建筑从泥土里生长出来。”
建筑确实能从泥土里生长出来吗?
哈尔滨大剧院这座建筑的话题性本身并不大,因为这种形态的建筑已经没有多少争议,无论是制造技术,投资规模,体量消解,空间结构。当我从一个非建筑师的视角观察它的时候,甚至我认为这是座略显平庸的建筑。但这种建筑极适合拍照,阳光下浓重阴影是体块壁垒分明既视感十足;阴霾天细腻的灰调衬以建筑的表皮柔和舒展;夜晚几束准确投光就能引人关注。

图:哈尔滨大剧院
这种建筑放哪里都不会讨人嫌。
建筑师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喜欢将项目植入意象,就像建筑师马岩松关于大剧院的口述:
一条丝带从地上缓缓升起成为一座雪峰;
采用铝板让建筑在四季都能适应环境;
凸起的包包隐喻皮肤上的颗粒;
轻盈的体态让它具有呼吸感;
玻璃天窗形成冰晶的感觉;
人们可以顺着坡道上到顶部的露天剧场眺望远方,这确实是一个很好地消解体量并且形成立面变化的亲民手段。
只是这样的建筑在松花江边的滩涂上出现,无论如何都是低调不下来的,更不是自然生长。这座建筑为哈尔滨这座北国城市提供了国际化的范本依据,带动了松北区周边地价攀升,这就是政府热衷于地标建筑的原因。
建筑师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赋予意象,并把这种意象强行和环境扯上关系,这也无可厚非。意象取材于周边空间的特质,符合所在区域的人文故事背景,建筑具有方向感和认同感。“人要定居下来,他必须在环境中能辨认方向并与环境认同”,诺伯格 . 舒尔茨所指建筑就是“场所精神”的形象化。建筑不仅仅是在设计表皮,意象,构造,材质,建筑应该发生实实在在的事体,建筑不再是强权是纪念,它应该是人居的背景,它从属与人的活动。我们见过太多的超脱现实的设计乌托邦,幻想中的与人关系亲密,但却没有做到实质。
什么是建筑的实质?
这个问题深奥晦涩可以列为哲学上无法消磨的回响,从维特鲁威到柯布西耶都在尝试着解释。回到老子所说“凿户牖以为室”没有意义,虽然这是实质,建筑的实质是让人定居下来。
再提密斯的“装饰就是罪恶”已明显过时,反装饰可得一时社会之需,没有装饰的建筑却无法长时间生存在人类情感中。一切建筑都是图形化的存在,图形本身具备意义,每个人的观察侧重点不同就产生不同的意义去向,而意义成为实质的表象,实质则因人的体验出现差异,实质只有一个。
努维尔的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将外表皮做到了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自动开合的形态,这只是建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体现。他的室内空间我并不认同,低矮和拥挤,自然采光也很不好。因为他将窗户做成了某种构造和意象。当建筑成为一个设计师的个人表现手段时,都已经产生了和人的行为上的疏远。

图:巴黎阿拉伯世界文化中心
就是隈研吾最喜欢说的“负建筑”,否定象征主义,他的作品依然充满表现性。他用朴实的木材、玻璃、石材营造超脱的形象,甚至他会做象形上的解释,以避免自己的设计过于风格与独特。“负建筑”的关键是你的建筑和周围空间融合的够不够深,没有文化和伦理上的断裂。

我们不谈扎哈是绕不过这个话题,她完全是个人主义下的极端设计,她的建筑脱离文化,地形和环境,她不重视人的感受,或者过分刺激人的感受,她以超大的扭曲体量成就了一个时代的需求,她以自我解释的形态满足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比如强行解释广州歌剧院是珠江边的两块圆润的砾石。她的学生马岩松也深得老师的精髓,将鄂尔多斯博物馆说成是戈壁荒漠上的石头,这里有一个承续关系。随后他的“北部湾一号”山形建筑,胡同里的不锈钢蛋等等都是出自这种逻辑。

现代意识让人对于未来陷入迷茫,其中之一就是未来的城市是什么形态?未来的建筑是什么面貌?城市是不是犹如科幻电影上描绘的那样出现立体化交通,链接太空的建筑,以及自由曲面犹如太空飞船一样的的居住状况?
在今天这个技术并不发达的时代,大面积的曲线运动代表着造价高昂以及技术难度系数倍增。这是消费时代的产物,所以 BIM 技术以及 GRC 材料成就了非线性建筑。只有人们想不到的造型而没有人们完成不了的建设。老实说我并不喜欢非线性参数化的室内,尤其是带有仿生学的室内。哈尔滨大剧院室内剧场犹如一条大白鲨的口腔内景,密布在墙壁、天花上的椭圆型孔洞类似于鲨鱼的唇吻鱼鳃。设计师到底先想造型还是先考虑环境的承载力,以及长时期的观众审美疲劳?怪异的空间只会更快让人厌倦。
我们可以将建筑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粹功能性,哪怕是一间铁皮房,都具备遮风挡雨的居住功用;一种是装饰性,它成为城市标志,如果历经战争和天灾还能存留,最后就能成为历史文物。装饰性的事物成为文明曾经发生过的痕迹,就像我们去看墨西哥的玛雅金字塔,伊拉克乌尔的塔庙,它们在当时都是辉映一方的伟大事物。无论是万神庙还是乾元殿一直到今天的哈尔滨大剧院,建筑都在彰显它的瞻仰功能。成为地标事件就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如果扎哈的建筑不倒,它也能成为这样的文化遗迹,纵然后来的建筑无论从形态和材料上远胜过她。但她是始作俑者,历史是由原创者开启的。同样学习扎哈的马岩松,如果走不出扎哈风格的羁绊,无论做的再好也都是一个模仿者,历史不会记住他。当然了,我这是苛求。
不可否认,大剧院的照明呈现出一种诗意化的设计,用洗练简易的手法明确了建筑在夜晚的呈现。在光的构成上形成了深邃,提神,层次分明的视感。在主观的建筑语境下依然有照明设计对于空间的解读,运动的曲面弧线,水平的转折节点,突出的表皮结构,照明设计卡准了几个关键点,控光准确,提炼出关键的符号,用更浓缩更抽象的光再现了建筑在白天的体量,内敛节省的做了设计。
正是因为照明设计的目的是再现建筑而不是重塑建筑,照明脱不了建筑的桎梏,照明设计师只需要研究好配光功率,表皮反射,灯具位置,投射角度,而在设计文创和艺术提炼上发挥的余地很少,于是照明设计成为建筑设计的附庸——光只为了照亮构造而存在。就像小剧场的水纹墙面,受光物已成,剩下的就是选择合适的光线切入角度,水平高低只看用光的巧妙与否。
以玩弄造型夸张、结构独特、善于打破叙事逻辑著称的建筑师弗兰克 . 盖里曾经说:“作为一个建筑师我相信我们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城市的未来不是赖特或者柯布西耶建造的,这些景象都会消失,已经建造起来的作品虽然有风格特点,但不解决社会问题。我认为在当今世界里,建筑艺术的唯一出路就是与信息传媒、计算机和人文艺术更加广泛地产生联系。”

图:弗兰克 . 盖里作品——华特·迪士尼音乐厅
当设计趋势已经走向以建筑为视觉的虚化背景,更多关注空间运动中的综合布局,建筑崇尚的是去标签,去地标,去纪念,去象征的时候,这才是从泥土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建筑,它不是空间中的唯一。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