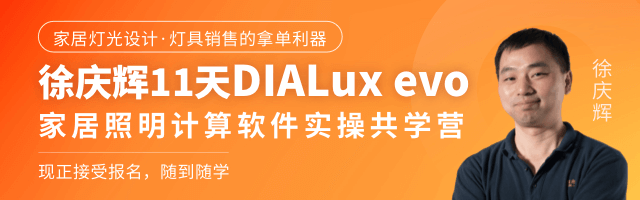这个春节,过得不太平静。
陈大华教授于1月21日驾鹤仙逝,享年77岁。听到这则消息后,我十分诧异,以为朋友和我开了个玩笑,但看到讣告后才知,已是天地两重天。

与陈教授虽非实名上的师生关系,但常年书信交流和来往,渐成私人关系上的老师和学生了。在我心里,他便是恩师,结交已过十五载。
与陈教授的第一次结识是在2004年,中山古镇。他被评为“2004首届中国照明行业十大人物”,从上海来古镇领奖的全过程,由我接待和专访,这是我们的第一面。时年62岁的他,精神矍铄,低调谦卑,一个劲地说,“给你们添麻烦了”。
自此以后,向陈教授的取经便成了家常便饭,而他从不厌其烦地予以耐心解答。如遇深奥处,他便用书信方式写下来寄给我详细阅读,细致入微,备受感动。
2009年7月17日,中国电光源之父蔡祖泉教授逝世。我受复旦大学电光源系所委托,给蔡祖泉泉教授撰写传记。从对蔡教授的生前回忆,到历史资料的收集,再到采访对象的预约,都是由陈教授由全程帮助;传记付印前,十余万字,他还一字一句地校稿,直到该书印制成册,快运到系所办公室。
写寄纸质书信是陈教授一生的习惯,哪怕在电子邮箱E-mail和社交即时通讯盛行的当下,书信依旧是最朴实、最真实、最亲切的交谈方式,正所谓:见字如面。
谨呈此前对陈教授的专访文章,当是缅怀他光明的一生。
再读书信,见字如面。愿安息。
陈大华:心怀中国,光明一生
 陈大华(1943.1━2020.1.21), 浙江宁波 ,教授(博导)。
陈大华(1943.1━2020.1.21), 浙江宁波 ,教授(博导)。
1965年2月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随后留校电光源研究所。
1982―1984公派赴德国基尔(Kiel)大学实验物理研究所学习;
1989―1990公派赴美国国家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IST)工作。
曾任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副系主任和系主任、电光源研究所副所长和所长。曾兼职中国照明学会副秘书长,上海照明学会副理事长和上海照明电器协会技术顾问,以及担任国内外近10家光源和照明学术杂志的编委和编委主任,还是国际学术机构欧洲建筑节能照明委员会和国际照明学会视觉委员会的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电光源的研制和开发,低温等离子体物理及其应用,以及照明和视觉科学,曾多次获学校和国家的奖励。先后主编和译著如“光源和照明”,“现代光源基础”,“光源电器原理及其应用”和“光源和照明英汉词典”等专业科技著作20本,总共约800万字。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和国内外学术会议发表科技论文约200余篇。
古老的复旦大学,桃李满天下。
周谷城、陈望道、颜福庆、苏步青、谭其骧、周予同、陈建功、朱东润、胡曲园、严北溟、张世禄、伍蠡甫、卢鹤绂、谢希德等著名大师与学者奠定了复旦雄厚的学术传统和基础。
谈家桢、吴浩青、谷超豪、胡和生、王迅、陈中伟、杨雄里、杨福家、汤钊猷、顾玉东、李大潜、陈灏珠、沈自尹、闻玉梅、王威琪、陆谷孙、章培恒等一大批知名专家,成为复旦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
于右任、邵力子、陈寅恪、竺可桢、张志让、李岚清等众多复旦杰出学子,为国家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也许,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在复旦29个直属院系中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但它是中国设有电光源和照明工程系的唯一高校,承载着国家电光源科技进步的领军任务,为中国电光源事业发展所贡献出来的力量,却是巨大的。蔡祖泉被尊为创始人,而他的弟子们亦是中国电光源事业从起步到发展到飞跃过程中的见证者、实践者和有力推动者。陈大华,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艰难起步的年代
尽管在1923年上海亚明灯泡厂制造的国产白炽灯已经在中国出现,但是,能拥有一只白炽灯,却非易事——对于80年代后出生的年轻人来说,这段艰难的历史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买一只白炽灯还需要“证明”。
“60年代,我们国家的光源电器起步异常困难。当时我们买白炽灯,要求出示已损坏的玻璃和灯头,才允许你买一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当时的人均灯泡数量是30-40人/只,灯泡供应不足。这就是60年前后中国光源电器领域的现状。”人们用“艰难的起步期”来形容那个年代的状况。
1943年出生的陈大华,祖籍浙江宁波。他生长在普通工人家庭。父亲是位邮局工人,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家里兄弟姐妹9个,他排行最小,小时候就随父母来到上海。父母的恩典、善良、识理和爱国,以及对子女的谆谆教导,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

陈大华的四个姐姐都是在1949年前参加革命,之后在不同的岗位上担任领导工作,对弟妹们的培养关怀备至,身教胜于言教。之后,陈大华的其他几位兄姐分别考进了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航空学院,而陈大华进入复旦大学学习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960年2月,陈大华在上海复兴中学读高三。
“陈大华,你出来一下。”有一天,正在上历史课的他,突然被班主任徐绚贞老师从教室里叫出来。
“你明天不要来上学了。”老师开头就说到。
陈大华一下子给这句话蒙了。“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从小学到中学,他在班上一直都算是学习成绩好、听话的学生,怎么今天突然被班主任通知不要来上学了?
“你今天赶紧收拾一下,明天就去复旦大学报到。”班主任接着说。
此时,他似乎有点忐忑不安:“老师,历史课还没上完,下个星期还要测验考试呢。”
“课你就不要再上了,赶紧收拾,明天就去复旦。”班主任重复了这句话。
“那我还能回来吗?”他追问。
“不用回来了。你到那里要好好听那里的老师的话。”
就这样,上海市200多名中学生从重点中学被抽调到了复旦大学,一部分被安排到物理系,一部分进了数学系。因为在60年代前后,国家将发展高科技、电子学、航空事业等列为当年社会的历史需求,要求加快人才培养。这些人当中,之后绝大多数已经成为院士、博导、教授、高工,甚至神州六号飞船总指挥,为祖国科技事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63年,陈大华就读大四时,开始进入由蔡祖泉领导的电光源实验室参加实验工作。1965年2月,正式从物理系电子物理专业毕业,并留校开始他的电光源事业生涯。
上世纪60年代初,尽管普通白炽灯能点亮普通家庭,但是我们中国在经济建设初期,搞很多的科学研究需要购买仪器,一套仪器的采购价要30—40万美金,但是备用光源有限。如果光源坏了,怎么办?中国还没有这些特殊需求的先进光源。
我们就向设备提供商希望购买1-2个备用光源,但是外商苛刻地提出:需要再买一台仪器,才配送光源。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蔡祖泉教授就认为,我们中国要有自己研发和制造的仪器光源,才不会受制于人。
蔡祖泉老师以前曾从事电真空研究,参与发明研制出X光管等工作,具备一定的基础。60年代,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室就在这种艰难的状况下,由蔡祖泉教授带领开始起步。这也是中国电光源事业迈出了自主创造和研究的第一步。它也是对中国人骨气和智慧的考验。
事实证明,这是正确和艰难的一步,更是十分有意义的新征程。
吹响进军新光源号角
第一个研究的光源产品是高压汞灯。
搞高压汞灯研发遇上了一个难题,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但那时国内无法生产出来。蔡祖泉老师就将厚厚的钼片放在铁砧上敲,像打铁一样,就是用这种最土的办法,把厚厚的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
大家敲了无数张钼片后,终于获得了达到标准的钼片,解决了金属和石英玻璃的真空密封问题。
当时国家条件差,粮食也比较紧缺,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原材料的研发,蔡祖泉老师每天从家里煮好稀饭带到实验室,通宵达旦地工作。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一批年轻人在实验室里工作,基本上没有白天和晚上、寒假和暑假。每天晚上加班,睡觉就在实验室的平台上睡。
但是,正是因为有这种奋斗和拼搏的精神,经过两年多的研究,最后第一只高压汞灯研制终于成功,为我国以后发展高强度气体放电系列新光源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这一消息当时在复旦大学校内引起很大的反响。1965年,复旦大学开全校党员大会,把高压汞灯挂在全校大礼堂最显眼的位置。后来,学校做了一个决定:成立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室,并且连续三年每年的元宵节举办一次灯会,展示我们的研究成果。
连续三年的灯会,让人们了解了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的动态。而高压汞灯的成功研制,为我国近代光源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965年,在上海人民广场上出现了一只灯,它把广场照亮得像是白天,许多人聚集在人民广场观看这一新生事物。人们不知道它的专业名称,就取名为“小太阳”——它就像一个人造太阳一样悬挂在上海的高空中。
这只灯,国家教育部希望送到北京去展出。为了保证送到北京的灯能有保障,全实验室的师生夜以继日地实验。由于点灯实验的整个过程中,在寿命期间内尽可能不熄灭,因此必须24小时轮流换班坚守岗位。
按照规定,晚上做实验是可以加餐的,二两饭、一些青菜、一些肉。这对于仍处于解决温饱问题时期的国人来说,这样的“待遇”已经是令人很高兴了,这是很大的享受。
晚上用餐时,实验室是必须留人的。这其中,我们也出过值得回忆的有趣事情:
我们几个人留在实验室,其他人出去加餐了。年轻人都爱睡觉,再加上连续几天的加班加点,大家都太疲倦了,所以就在实验室里睡着了。等其他的工作人员回来敲门,发现没人应。他们连续敲门,还是没人反应。这时,他们就紧张了,里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但是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灯还亮着,于是,他们就翻墙进来,发现里面的人全部睡着了,结果这几位睡觉的人被挨批评了。
连续一段时间的亮灯实验,证明了这个“小太阳”完全可以送到北京去展出。但是由于灯太长,就坐在卡车上,把灯扛在肩上,先送到火车站,再坐一天一夜的火车送到北京。整个过程,他们一路护航。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只“小太阳”的专业名词叫“长弧氙灯”,5米长,直径较粗,功率达到20万瓦,超过当时国际上10万瓦的最大功率值。20万瓦的功率产生的热量是极大的,只要小虫一碰到这只灯是必死无疑,在做实验时,长弧氙灯周围堆积起了几公分厚的小虫残骸。
新光源发展时期
1966年初,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等东南亚国家访问期间,当时中国的新闻记者用的还是那种老式放炮式的新闻灯,像排球那么大,携带起来很不方便,而且还引起了爆炸事故。在缅甸,刘少奇主席看到缅甸的新闻记者用的是国外新研究出的碘钨灯,同样发光很强,却只有铅笔那么大小。
刘少奇将这一发现记在了心里。回国后,他立即马上召集中国的相关科研人员,问中国人能不能自己研发?复旦大学作为光源科研机构,被委任作为研究单位之一。结果,在蔡祖泉的带领下,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研制成功,提供给我国新闻和摄影单位使用。
60年代后期,复旦大学对电光源的研究继续开展。最明显的现象是,以前看电影,电影屏幕经常会发生熄掉中断现象,放映员又要重新点上光源才能继续放映,一部电影会发生中断事故,而且电影画面效果很昏暗。更重要的是,这种旧光源一点亮时,其电弧容易散发出一种有毒的气体,造成人体伤害和环境污染。
为了满足电影放映需求,复旦大学电光源所开始研制电影新光源。我们一般是在晚上10点之后到电影院,等电影放完后才能试验新光源。日复一日。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复实验,在70年代中期,电影和舞台新光源被研发出来,而且经过不断的改良,技术也日渐提高,先后研制出水冷短弧氙灯和风冷短弧氙灯两种新光源。
短弧氙灯刚开始研发出来时,放映效果很好,上海的影院都想用这种新光源。但是有些人抱怨价格太贵,碳晶棒只要几块钱,而氙灯要几百块钱。
但是,事实能证明一切。为了推广,当时大家把在电影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晚上请到电影院观看试映效果,用两种不同的光源,放映相同的电影内容,对比结果很快就出来了:炭棒放出来的电影效果就像黄昏,短弧氙灯的效果就像晨光明媚的阳光,新光源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但是,这还没有完全消除影院的顾虑,这其中涉及到光源产品的性价比问题。他们还在考虑:值不值得去用短弧氙灯?
于是,当时又采取了一种办法,并给影院领导算了一笔帐:
你原本用炭棒的成本每对只要1.5元/只,寿命为一个小时。而短弧氙灯单价是1000元/只,现在免费送给你用。你每放一个小时就给1元钱,等短弧氙灯用了1000小时,收回了1000块钱的预计成本,这只氙灯都送给你了,不要你的钱了。这种办法就好比现在社会上积极推广的“能源管理合同模式”——产生多赢局面。
当然,这种办法必然就对短弧氙灯的质量提出很高的要求,寿命一定要长,不然连单支成本都收不回来。如果短弧氙灯的使用寿命只有10个小时,电影院却要支付1000元的费用,那肯定是不合算了。
最终使用结果是:短弧氙灯的平均寿命超过1000小时,有的甚至超过2000小时。这种办法不仅使电影院的放映效果得到彻底的改善,而且使短弧氙灯新光源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和应用。
现在国内还有哪家影院还在用碳晶棒?全国家家电影院都是用短弧氙灯新光源放电影。因此,这种灯得到轻工部颁发的光源金质奖。时至今日,当我们坐在宽敞豪华的电影院里观看大片时,有不少人还不知道这种视觉效果背后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程。
之后,这种新光源不仅得到影院认可,还大量出口。这一典型的例子也足以证明中国自己研发和制造的光源产品被世界所接纳和认可。
由此,我们中国的光源产业也由一个艰难起步期走向了一个逐步发展的阶段。
百花齐放的春天
如果要把中国电光源与照明产业的发展做一个阶段性划分的话,60年代前,是贫瘠期;60—70年代,是艰难起步期;80年代是发展期;90年代是高速成长期。80年代步入发展阶段,是因为借助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东风。
1978年,国家正式任命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室为国家级研究所。当时,复旦大学内被国家任命的四个国家级实验研究所只有四个:一个是苏步青的数学研究所;一个是谈家桢的遗传研究所;一个是谢希德的物理研究所;第四个就是蔡祖泉的电光源研究所。
比较客观地说,全国新光源的第一个样品几乎都出在复旦,无论是高压汞灯、碘钨灯、长弧氙灯、短弧氙灯,还是后来的高压钠灯、金属卤化物灯、紧凑型荧光灯、微波硫灯等,都是如此。
这一级别的定性,不仅是对复旦大学为新中国电光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其未来的历史使命寄予了厚望。邓小平当年参观高校科技成果光源陈列品时,就给予了高度认可。
但是,蔡祖泉和他的弟子们认为,一朵花开不是春天,要百花齐放。一个偌大的中国,若只靠一个电光源研究室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于是,为了在全国推广及普及电光源技术与产品,1984年,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创办了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并开设培训班,大量宣传和推广光源技术和理论,把基层光源科技人员请到复旦来,手把手地把技术告诉他们,把测试的数据、报告、技术等内容一一传授给他们。若遇到问题,复旦负责任且毫无保留地教会基层人员。
这样做的最大社会价值就是使中国电光源水平得到迅速全面的提高,收获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在系所创办时,陈大华刚从德国进修归来,承接了学校任命的副系主任兼副所长工作。
坚决回国,回到复旦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世界的大门逐渐互相敞开。1982到1984年,陈大华第一次被公派到德国Kiel(基尔)大学实验物理技术研究所进修,学习国外更先进的科研技术。在德国,陈大华得到了德国导师柯西教授的指导和悉心帮助。
到了1984年,进修期满时,德国导师想把陈大华留在德国,但最后还是被他谢绝了,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而1984年,正是复旦大学照明与工程系成立之年。初创的科系需要大批师资力量,陈大华心怀复旦和中国,回到了他的教学岗位上。

1989年到1990年,陈大华又被派到美国科技和标准研究院(NTST)工作。在合同期满后,在NTST人力资源部领导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张绿卡和一份已经拟好的邀请函,希望陈大华能留在美国。
而此时,陈大华更清楚的知道自己内心的选择。最后,他对NIST办公室负责人说:
“感谢你们提供的经费和参与你们的研究工作,你们是我的‘小老板’。而我的‘大老板’是‘复旦’,我的事业在中国,没有我的国家和人民,没有复旦大学,我是不可能到这里来的,所以我得问过我的大老板再做决定。”
他巧妙而又委婉地谢绝了NIST的挽留。
自从美国回国后的1999年到2004年期间,陈大华担任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主任和电光源研究所所长。他与全体师生们一起为我国电光源事业的振兴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并使系所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体现陈大华心中时刻装着祖国还有另外一件不为大多数所知的事情:1992年8月,他应邀出席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光源科技研讨会,这是国际电光源科技领域最高层级的学术会议,也是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全球电光源科技精英相聚切磋交流的盛会,宗旨是为全世界从事电光源研制和发展的科研人员对共同关注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提供一个相互讨论和交流的论坛,并通过会议展示国际电光源的最新发展和成就。陈大华为能出席这次会议感到幸运。
但是,此时此刻,陈大华身在布达佩斯,心里想着的却是祖国。他心想:如果能让没有机会参加国际电光源科技研讨会的国内同仁也能分享会议的成果,对我国电光源科技的发展该是一件多有意义的事情。
在此前,第四届会议的资料,由于经费和其他条件的制约,只印了少量的油印本,未能得到广泛交流和传播,十分遗憾。于是,在团队蔡祖泉、副团长甘子光两位教授的倡议下,陈大华挑起了这副重担。

回国后,他立即投入到翻译文集的策划和组织工作中,从翻译、校对、出版、发行到筹集资金全力以赴。他善于团结同仁、群策群力,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把国内电光源界众多专家、学者、工程师、研究生和学生都组织到这个庞大、纷繁、浩瀚的学术论文翻译工作中来。
经过集体的努力,终于以短短3个月的时间,在他的主持下,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第6届国际电光源科技研讨会》译文集。随后几年,他还相继主持了第7届、第9届国际电光源科技研讨会译文集的编撰工作,为中国从事电光源科研人员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材料。
桃李满天下
岁月如梭,时光流逝,他在杏坛执教已45年,把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他所执著追求的光明事业中,把一批又一批的本科生、硕士、博士研究生送上了国内外电光源科研、生产第一线,眼看着学生们的进步、成长,就像一棵棵播种的科技种子,根植在电光源科技领域的土壤上,将给电光源事业的繁荣带来绚丽的春天。他感到无限欣慰,内心充满了喜悦。
他无悔于自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也无悔于对光明事业的选择,他一直自豪地认为,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人类播种光明、为促进人类文明的事业,是他最大的幸福。
看着一批批学子,从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毕业之后,走上国内外大公司,科研和教育单位的岗位,并不断带来优秀成绩,这是他最大的自豪。
他所带的一位博士生,正式毕业前到美国GE中国总部应聘。
等这位学生刚从GE公司大门走出来后,GE中国区负责人就立即打电话给陈大华:“陈教授,您的这位学生,我们公司要定了。刚才没直接告诉他,是要等美国总部签字批准,务请理解。”
还有他的一位博士生到德国西门子应聘研发部门负责人一职位。双方交谈后,西门子公司立即表态说,非常欢迎这样的年轻优秀人才加盟。
这仅仅是两个小案例,但是足以体现复旦大学光源与照明工程系对人才培养的价值。从创办科系到现在,大部分学生都在重要岗位上发挥出他们的价值。
这是陈大华等老师们的骄傲。但他却有另一番忧虑:
中国的电光源事业才刚刚起步,需要大量高素质的人才。如果这些人才全部流到国际大公司里,中国本土企业的人才从何而寻?所以,每到学生毕业时,他都积极地鼓励学生加入中国照明企业当中去,为中国电光源贡献力量和智慧,这是中国企业之所需,也是中国照明产业之期盼。
现在国家在电光源技术人才方面还是缺乏,我们的责任还重大,应该摸索新的教学方法,不能沿着老路,要不断创新。当前形势正处于一个不进则退的环境中,需要我们继续努力和不断提高。
2008年,由陈大华主编的《光源与照明英汉词典》正式出版,这是中国照明与光源行业第一本英汉词典。该词典一共收录了4万余词条共90万字,全书656页,耗时三年。
为什么大家要编辑出版这本词典?
——光源与照明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的领域,它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尤其是在当今节能环保和减排降耗的历史潮流下,绿色照明就更显示出其重要性。随着我国光源与照明的长足进步和走向世界,国际交流频繁,人们在科技交流和商贸合作中对这一领域的中英文确切翻译也提出了迫切要求,这就是我们尝试编写这本词典的初衷。

至暮年时,他也依然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他可谓中国电光源界的“高产作家”,由他编著、翻译的专业科学著作约20余本,总字数约800万字,均在国内外电光源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影响。
他经常说自己很幸运。如果说自己这一生还有一点成就的话,应归功于导师的教诲、同仁的帮助、亲属的支持,也应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还可以发挥出的一点光和热,还能发挥出一点作用。但是我认识到,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必须让路给年轻人,随时准备接受退休。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人要知老但不畏老。要客观承认自老,必须为年轻人让出位置,要作为年轻人的阶梯,做他们的铺路石,让年轻人踩着我们的肩膀站得更高。社会能进步,能发展,肯定是年轻人胜过我们。假如不是这样,国家就不会有希望,未来就不能更美好。”
总结已经走过的路,他感到有四条选择,体现了老天是很恩惠的:
“一是我选择了好的学校,选择了复旦;二是我选择了好的老师,蔡祖泉老师教育和培养我们,我们是他一辈子的学生,我22岁跟着老师,老师一生对学生的教诲是我们的荣幸;三是我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一直以来,学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陪我们看病、关心和爱护。能看着他们走向理想的职业岗位,并在岗位上做出贡献,值得我们骄傲;四是选择了光源行业,这是一个有生命力的行业,朝阳产业、光明的事业。”
斯人已逝,甚是想念。再次忆起他和蔡祖泉教授共同的期望:要让中国由世界光源大国变成一个世界强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前辈们心系产业,胸怀祖国,奋斗一生,一直没有放弃产业报国的伟大梦想。我们应该沿着这条道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终有一日,强国的梦想一定会实现。